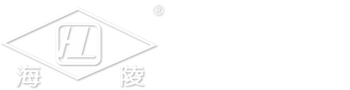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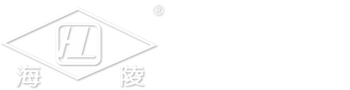
我國現行標準體系是立足本土國情、厚植改革沃土、歷經長期標準化實踐探索與制度創新逐步凝練而成的系統性成果,其演進脈絡深度契合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需求與科技創新的變革趨勢。從標準供給的底層邏輯與治理效能來看,該體系呈現出“二元供給主體協同驅動、全域標準化深度覆蓋”的典型特征,既體現了標準化治理的本土化智慧,又彰顯了面向未來的適應性張力。
那么,如何準確理解標準供給二元結構的核心要義,需要把握以下三個關鍵維度:
一是切實厘清,并正確領會標準供給所形成的二元結構框架。
當前,我國現行的標準體系呈現為政府頒布標準與市場自主制定標準并行的二元架構。在這一架構下,政府頒布的標準體系涵蓋國家標準、行業標準以及地方標準,主要發揮基礎性、引領性作用;市場自主制定的標準則包括團體標準與企業標準,更側重于響應市場需求、推動技術創新。兩者在功能定位上各有側重,但又通過技術銜接、資源共享等方式緊密協作,共同構建起層次分明、動態平衡的標準體系生態。
在政府頒布標準與市場自主制定標準的協同機制中,存在雙向互動的規范邏輯。一方面,市場主體在制定團體標準或企業標準時,必須以強制性國家標準的技術底線為基準,同時可合理吸納推薦性標準的技術成果,確保標準體系的合規性與兼容性;另一方面,當市場自主標準在特定領域形成技術領先優勢或產業共識時,政府標準制定機構可通過"采信"機制將其納入標準體系,實現標準化資源的優化配置。
如今,我國標準體系已進入深化改革的關鍵階段,部分技術領域仍存在政府頒布標準數量較多、市場自主標準發展不均衡的現象。面對政府與市場兩個供給渠道,如何更好地平衡國家標準化與經濟社會需求之間的關系,成為各研究機構、先進企業的關注焦點。
在規模結構方面,政府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的立法精神,對現有標準體系進行系統性梳理,通過廢止滯后標準、轉移適宜標準至社會團體等舉措,推動政府標準向"少而精"方向轉型;在協同發展方面,將建立覆蓋標準制定、實施、評估全流程的協同機制,既保障政府標準的基礎性、權威性,又激發市場標準的創新性、靈活性,最終形成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技術演進為驅動、以產業協同為支撐的新型標準體系。
二是聚焦團體標準這一關鍵領域,精準把握市場供給標準的改革方向。
《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明確提出,“要大力拓展市場主體標準化空間,進一步優化政府頒布標準和市場自主制定標準的二元結構,大幅提升市場自主制定標準的比重”。在標準化體系的“二元架構”中,政府強制性標準宛如一道堅實的底線屏障,發揮著兜底保障作用。而團體標準作為“促先進、促創新、促競爭”的先鋒力量,其覆蓋領域與占比規模也將會隨著標準化體系的逐步完善而進一步拓展延伸。
在“保底線”標準范疇之外,給予市場自主制定標準發展空間,讓市場機制在標準供給中扮演更為核心的角色,最大限度地激發市場活力,提升其對標準供給的支撐效能。這樣做不僅契合市場需求,更是我國標準化事業發展的必然選擇,同時也是順應國際標準化發展主流經驗與趨勢的重要舉措。
三是以市場驅動型團體標準為引擎,賦能標準化治理體系現代化轉型。
在"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協同共治的框架下,通過構建"政府主導基礎標準筑牢底線、市場主導團體標準激活創新"的雙向賦能機制,推動標準體系從行政主導型向需求響應型躍遷。具體而言,需以"雙輪驅動"實現三重突破:
1、技術迭代加速機制
通過建立"強制性國家標準錨定安全底線+推薦性國家標準構筑技術基準+團體標準突破創新前沿"的三級技術傳導體系,形成"技術突破-標準孵化-產業應用"的閉環鏈條。例如,在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等前沿領域,鼓勵龍頭企業、行業協會牽頭制定高于國標的團體標準,倒逼相關技術和應用向高水平方向發展,破解傳統標準滯后于技術發展的治理困局。
2、資源配置優化機制
以團體標準為載體搭建"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平臺,通過標準聯合制定,引導社會資本向戰略性新興產業集聚。例如,在智能制造、工業等領域依托團體標準構建模塊化技術接口,推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從"物理集聚"轉向"標準協同",實現資源要素的最優配置。
3、治理效能提升機制
國家標準與團體標準在治理能效提升中形成了“基礎支撐+創新賦能”的協同互補體系,通過差異化定位與動態銜接機制,實現了治理效能的螺旋式躍升。國家標準作為社會治理的“壓艙石”,以強制性與推薦性條款劃定底線框架,為市場活動提供確定性規則;團體標準則作為技術治理的“探路者”,可快速響應新興技術迭代與細分領域需求,制定高于國標的技術指標,填補國家標準修訂周期中的“治理真空”。
二者協同的核心在于構建“雙向傳導、梯度提升”的治理閉環,這種“剛柔并濟”的協同模式,既保障了治理體系的穩定性,又釋放了市場主體的創新動能,成為提升治理現代化水平的關鍵路徑。
二元標準體系的戰略迭代,本質是以市場化邏輯重構標準化治理體系,推動政府與市場在標準供給中實現“守底線”與“拉高線”的動態再平衡。這一進程絕非傳統標準的“存量替代”,而是通過“政府歸位筑底、市場破界拓新”的協同轉型,實現治理范式的結構性躍遷。未來,隨著二元標準體系的逐步深化,中國標準化治理將步入“競合共生”的新階段。而這一標準體系的重構,將構筑起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技術護城河”,促使團體標準向“高價值、強韌性、全球化”方向發展。